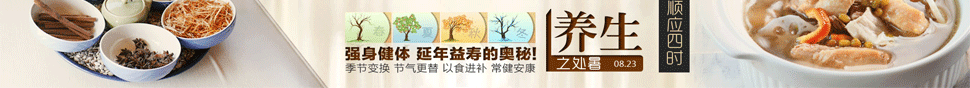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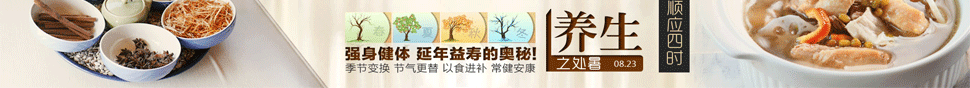
我们了解到,蒋家每天通常要杀十三头猪,八十岁的廖承国当时为蒋家记流水账,整日忙碌,买肉的多是为纱厂运煤、棉的船家。他们逆沅水而上,一到码头就得喝“到岸酒”,一次买下半边猪,一度带动了小巷的繁荣。
船家乐意与蒋家做生意,是因蒋家价格地道,做账实在。受战局影响,物价波动大,上午可买一斗米下午只买半斗的情况时有发生。蒋家的做法是,买家记账是5块1斤,即便结账时达20块1斤,也只按记账时价算。当然,杀行供给纱厂的肉并不少。廖承国的一位族弟曾一度单日从纱厂的排水口捞起斤肥肉,再炼油售出,因此发家,可称作“地沟油”行业先驱。这一奇观滋生于战时经济的大环境,也是安纱厂当时的一个缩影。
动乱的世界,安江一时堪称小上海
来自湘潭的年轻人黎泽重随姐夫一路赶到安江,已是年,他在安江农场住了下来。那是一座别墅式的公馆,也叫唐公馆,为安纱厂厂长唐伯球的住所。随后,其姐夫罗学宪去沅陵、常德一带采购棉花。
他后来一度掌管全厂的原料采购,曾到安江、浦市、桃源、津市、南县等地收购原棉,甚至还从洛阳及美国购买原棉。自年11月25日复工,安纱厂的产量就不断扩大。据《安纱厂志》记载,第二年就出产了棉纱件,棉布万米,第三年又新建了一个漂染工场,购置8口染缸和1台烘布机,并且接收了黔阳煤矿。
对黎泽重而言,他感兴趣的是安江的繁华世界。南来北往的人都聚集于此,不少北方人在这里开饺子馆、面馆,还有来自江浙的商号,以及国民党开赴衡阳的军队,也有撤下了的伤兵。不少美国飞行员还从芷江机场来此采购,亨德利、大三元、盛德庄、狗不理包子等随处可见。此外,京剧团、杂剧团、湘剧团、花鼓戏剧团等在街头轮回演出。
在安江镇的大马路上,由于人多房少,很快用楠竹盖起了简易房子。一时间形成了下马路街,堪称小上海,仅污水沟就达到3米宽,还设有3个妓院。廖承国当时住在安江镇小溪坑村,他经常到安纱厂前门理发店的豆腐摊买油条。卖油条的是一位外地人,免费给理发店老板打工。直到一些年后,大家才知道这个外地人是一名地下党员。
无论是黎泽重,还是廖承国,他们所看到的都属安纱厂外的情景。这一切似乎与安纱厂无关,实际上却是安纱厂所在的真实环境。在这样的战时社会经济中,每一个安纱厂的人与之抹不开关系。
现年80岁的廖承国到纱厂子弟学校入学是在年,老师黄雪梅突然有一天让班上的孩子不要乱跑,因为纱厂河对岸的难民所里爆发了瘟疫。据说,有人从岳阳那过来,“遭了日军的细菌战,一下子死了不少人”。这令学校对孩子们严加管控。
7月18日,洪江市安江镇,沅江边的安江纺织厂。这里的地名叫作马勺塘,因为地基平坦,且深处雪峰山腹地,不易遭日机空袭,湖南第一纺纱厂搬迁至此。
沅江边的安江纺织厂。这里的地名叫作马勺塘,因为地基平坦,且深处雪峰山腹地,不易遭日机空袭,湖南第一纺纱厂搬迁至此。
警报声中生产,沅水上终日奔忙的运纱船
“挑煤的日子很苦啊!”年7月19日上午,88岁的廖承值刚从菜地回来,一进屋就腰板笔直地坐在厅屋,尽管耳朵有点背,但他说起以前的安江纱厂一下子收不住话匣。由于父亲较早病故,廖承值不到20岁就开始给纱厂挑煤谋生。每担煤约斤,从河岸挑至纱厂的锅炉房有2公里的距离,挑1吨可得元国币,一天最多时能收入元,可买得1斗米。这在当时算不错的收入。
通常而言,只是在内部职工忙不过来的时候,纱厂才会请外面的人帮忙。廖承值挑煤进厂时,厂里会给其发放一张标牌。像他这样的挑煤人,在当时还有一些来自湘乡、涟源、邵阳、湘潭的人。这足以说明纱厂的生产极为繁忙,仅煤炭每月就需1多吨。廖承值在纱厂打工最多是从年开始的,一直持续了4年多。
和廖承值一样,李长生的父亲当时也时常到纱厂担煤。70年前的安江,安纱厂周边云集了大批驻军,如中国陆军第四方面军、新六军等。廖承值印象最深的是,廖氏族人招待了新六军军长廖耀湘,他在廖氏祠堂里住了45天。某一晚,日军飞机袭来,安纱厂里的汽笛骤然响起,人们赶紧将灯火熄灭,进而躲过日军轰炸。廖耀湘撤军时特意赠了条枪给廖氏族人。至今,安纱厂内的汽笛高塔依旧耸立。它当年发出的警报可以涵盖整个安江镇,成为当地唯一的防空警报。这也成为很多老安江人对纱厂在那一年代最深的记忆。
至年初,随着纱厂产量不断提升,运输逐渐繁忙起来。令廖承值印象深刻的是,纱厂的运输队有5辆大蓬卡车,载重有14吨,以烧木炭和酒精为动力。若是早上八点出发,那么就得六点开始热车,几乎每天清晨,人们都会看到纱厂车队忙碌的身影。此外,纱厂还有载重65吨的驳船2只。不过,仅仅依靠纱厂自身的运输能力是远不能满足生产所需的。当时60吨以上的船不少于70条,终日奔波于沅水之上,为纱厂运送物资。
两封密电中的纱厂:充当战事救火队
安纱厂究竟有多重要,不妨先看湖南省档案馆所藏的两份密电。年7月31日,由军政部发给湖南省政府的电文中称,“战时兵员激增,本部筹办服装应需大量纱布,不易采购,内地公私纱各厂供给军用,相差仍钜。本部驻沅陵第二被服厂就近提用”。此后的年7月15日,军政部军工厂厂长赵中丞直接给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发来电报,请求其转电安纱厂,按照当月牌价改拨十四支纱30件应需用。
可以说,几乎每当军用棉被吃紧之时,安纱厂总是充当救火队的角色。尤其是随着战事的推进,国土不断沦陷,中国能控制的纱棉产量逐年减少,偏居湘西的安纱厂重要性愈发显现。至年5月,正值长沙会战激烈之时,位于沅陵的军政部第二被服厂再一次请求从安纱厂提运件棉布,但直到当年11月18日尚未交付货款,这迫使安纱厂发出了一份不客气的电文,“该项货款限于月底付清,否则该布取消提运”。
在湖南第一纱厂的供货清单上,分别为军警,卫生治疗及病人衣被,公务人员,全省公私学校,各县民生工厂,及注册有案之工商团体。这一点在年1至9月的销量统计表中一目了然,安纱厂在3月份就分别往军政部第十被服厂运出件,另有件军部特供,另有少量棉纱供给民用商号,包括沅陵、洪江、重庆、衡阳、晃县、安江,以洪江较多。
由于洪江自古水陆交通便利,商业发达,自湖南第一纺纱厂迁至安江后,当地商贩发现安江纱厂生产的棉纱运往贵阳等地出售,利润非常可观,纷纷从纱厂进货,再由挑夫经芷江、三穗到镇远,再改用骡马驼运到贵阳等地。
日夜生产的安纱厂在某些人眼里,无异于一块肥肉。一些上了年纪的安江人都记得,曾有一位叫潘壮飞的匪首,为现在的怀化中方人氏,娶有一位“双枪老太婆”,曾一度到纱厂来抓女职工、打劫钱物,但因沅水河上无桥受阻,只能隔河放枪。
尽管工厂日夜加班加点,依旧不能满足当时军民对棉纱的需求。至年,另外一个纱厂开始出现在安江。
一缕烽烟
一座墓和它的守墓人
大约年,“我父亲当时认识了一个金老头,他们好像是福建那边过来的”。李长生所说的“金老头”叫金陆生,生平籍贯不详,但在安江广为人知。年7月20日晌午,李长生领着我们一行来到安江镇黄花坪村田禾冲的一块菜地,拨开一丛南瓜藤蔓,露出一处墓丘。这正是金陆生夫妇所守的墓,夫妇俩先后于年去世,生前交待李长生把墓守好。
至今,李长生时常会上来查看。至于墓主是谁,碑文上只是刻有“海军陆战队一旅一团三营九连上尉连长陈骏銮”。没有谁知道金陆生夫妇与陈骏有何关系。
江湖恩怨
为何耗资巨大建第二纱厂
位于现今安江纺纱厂内,立有一块由时任厂长唐伯球和副厂长雷泽榴合写的碑文,详述迁建纱厂的不易。看起来,两人合作精诚,其实不然。
年,位于安纱厂下游4公里处的沅水河边,建起了一座新的纱厂,被命名为湖南第二纺织厂。建厂所用的纱锭是从遗留在柳林汊的设备中清理出来的,所建数十栋厂房、宿舍要比安纱厂高出一档次。其中尤为难得的是,厂内办公楼是一栋鱼鳞杉板房。这种建筑形制与位于现今安江农校内的中美联合作战司令部的办公楼相同,属当时高档房屋。那么,正当前线战事吃紧,后方为何还要耗资巨大建造一个新厂?
在当年呈报省建设厅的公文里,安纱厂给出的理由是新建一个分厂,可以减小目标,以防空袭。而实际上,力主新建分厂的是雷泽榴。据《安纱厂志》的说法,雷泽榴不安于副职,与唐伯球有一些矛盾。雷与时任国民党湖南省主席薛岳为同乡,也是其老部下,唐伯球无奈之下请辞厂长,雷泽榴进而积极提议建造第二纺织厂。
至年2月,省建设厅正式下文,派唐伯球、雷泽榴等为第二厂筹备委员,唐为主任。在纱厂下游四公里的大沙坪筹建湖南第二纺织厂,于第二年建成。二厂的作用究竟有多大,尚无确切的记载。据廖承值回忆,他一度和当地小溪坑的村民到二厂挑纱,用篾条包装,80斤一件,送到本厂织布车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二厂只是完成制纱这一环节,由于交通不便,得请民工挑送纱料。此外,由于二厂地处较为偏僻,使得那些下班较晚的女职工需走4公里远的夜路,时常担惊受怕。
年4月,该厂爆发了一场冲突,众多职工围堵厂长雷泽榴。原来日军进至雪峰山下,安江形势危急。厂方奉第四方面军司令王耀武之令停业疏散,但当职工要求发给疏散费时,厂长雷泽榴一再拖延,这令职工群情激奋。最终,雷泽榴只给工人下发约一个人维持一个月的伙食费用。这笔可怜的费用只够工人疏散到安最远不过泸溪一带。
随着工人散去,湖南第二纺织厂的命运宣告终结,于年6月与第一厂合并,成为大沙坪分厂。如果说二厂在战乱遭遇短命,那么,这个时候的另外一个厂则堪称苦难之中。
来源|潇湘晨报
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个上一篇下一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