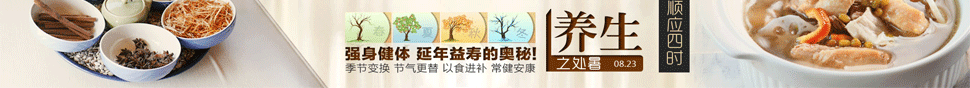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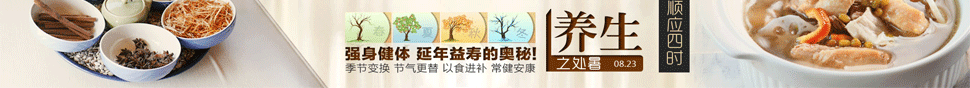
带你走进
感谢陪伴
未来不散
阅读下面的材料,根据要求写作。
一城山水养育一方人。你或许来自美丽的泉城—济南,或许来自古九州之首的青州,或许来自秀美的西湖之畔--杭州,或许来自东瓯名城—温州,或许来自港通天下的宁波,抑或来自依山傍水的丽水。
每一座城市都有属于它的自然特征、风土民情、历史文化、著名人物等;这座城市也保留着你的某种记忆与情感,或许是一段难忘的故事,又或是它对你有着特殊的意义。
请你以“带你走进______(济南、青州、杭州、温州、宁波、丽水)”为题,写一篇不少于字的文章。
带你走进丽水
高一(3)班张起瑜
我是丽水人,我妈妈是丽水人,我爸爸是丽水人,我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是丽水人。人有时就是这么奇怪,对自己的家耿耿于怀,纵有千般不好,还是什么事都想着她。因此虽然可以自己选城市写这篇东西,我想了好久,还是写了这个估计会落俗套的地方。
恕我直言,丽水城真的不好玩。这样半旧不新的小城往地图上随便画一笔就能圈进十几个。市旅游局煞费苦心建了几个景点,二期项目还没开建一期就荒废了--人们大都在资本家的“”工作制压迫下生存,又有谁愿意去几个毫无特色的景点呢?
要看丽水的美景,还得到下面的小地方去。
先说说遂昌。以前对她的印象仅限于金矿。第一次去,战战兢兢地坐着矿车,穿过一个很长的山洞,看到了在玻璃柜里的一些闪闪发光的东西和数不尽的人头。晕头转向走了一遭,稀里糊涂地便出来了。只记得外面的儿童乐园挺好玩。后来又陪着慕名而来的友人逛了几次,发现全是卖金银的商店,愈发觉得索然无味。
我对于遂昌是有些愧疚的。相比于在高速入口就昭然立好的金矿标牌,她的一位名人显得如此渺小和无闻。
汤显祖在遂昌任知县时写了《牡丹亭》。
曾有一段时间比较喜欢昆曲,被母亲骂说没骨气。偶然了解到遂昌有汤显祖的纪念馆,就忙乘车过去。在我国,但凡一个地方与某名人搭了点关系,就要拼命宣传。汤显祖在江西的家乡也建了纪念馆,但修得像皇宫,偏又没人去,阴森森的像鬼屋,在此点上也许真该学学遂昌。遂昌的馆不大,没有一大堆压人喘不过气的宣讲。古朴的小园,又恰是暮春,真有一番“良辰美景奈何天”之感。附近老人吊水磨嗓子“咿ㄧㄧ呀”,并不好听,但竟如此顺耳。一个人漫步园中,细想着当年汤显祖在此作词。望里青山,眼底残春,杨花如雪,芜亭阒寂。我不想同评论家那般分析《牡丹亭》的写作背景,只是无端觉得,在这里写出旷古名剧简直是从创世起就策划的一场大戏,汤显祖本人也在其中。真应了句老话“莫笑戏子痴,戏中戏外皆是客”。戏子长久以来被指摘为水性杨花,却不知有多少误读,汤显祖也一样。以前读《红楼梦》,不知为何唱本为禁书。如今看来,在那个年代能读剧,已是叛逆至极,何况作者!
我还欠遂昌一场纯正的昆曲,迟早是要听的。
再说说松阳县。宣传说她文化和自然并重,但我一直觉得她只有景。以前旅游没发展的时候,山里的村庄我是不屑去的。这里也要讽刺我的小资主义,一旦什么平田,西坑一类的村开发了,做了一些“网红”的民宿,就迫不及待地想去。江南山里的村子很秀气,别说那小桥流水,单是黎明山间的竹林和晨雾,就很令我向往了。虽如今有了旅游,也不像那些闻名的古镇般己经变了味道。一次去平田,狭窄的路上碰到了挑水的尼姑,我听长辈说尼姑晦气,就想闪到一边。没想到她先让开了,轻声道:“您小心脚下”。我经过时还微微欠了欠身。后来路过庙,进去逛了逛。村里的屋子大多已经改建了,只有小庙破破的,堆着些建筑剩材。佛像歪歪斜斜,有些傻气地笑着,一边放着一个功德箱。我觉得好笑,这破庙还有人捐款?松阳的民宿名字都很美,什么“云上平田”一类在全国都小有名气,虽然贵得咋舌,却也不同其他地方般势利。出了小庙不远就有处民宿,坐在露台的藤椅上,一旁是小瀑布,前方是山间翠竹云海。点一杯上好的银猴贡茶,同从大城市里跑来开店的老板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兴起了就拿出吉他古琴,也不讲究,想弹什么弹什么。此般一转眼就是一下午。
丽水还有些好玩的地方,譬如云和的梯田,武义的温泉。不过在全国其他处也能找到类似的,为了避免太像流水帐及耽误我玩的时间,便不一一说了。丽水就是这样,她以前很穷,现在在浙江也算得上穷,但总有些东西值得你去发现,进而感叹:“哪里去找这样的好地方呢?”
听说现在破庙已经改成餐厅,旅客反映到村里玩没有地方吃饭,就改了。旅游局本以为尼姑的思想工作难做,派了专人去。没想到尼姑很爽快地答应了,也没要政府的搬迁屋,到山里当苦行比丘尼去了。
后来餐厅里添了免费供应的凉茶。
人们都说凉茶铺是尼姑用庙的善款买的。
带你走进兰州
高一(3)班郑惠文
一条河,一座桥,一碗拉面,一份杂志,无不唤醒了我对遥远的兰州的回忆,回忆起了某一天的夏日,我乘坐着列车奔向遥远的兰州。
这一路是横无际涯的黄土,这一路是连绵不断的黄山。我即将到达的城市就是被人们称作“金城”的兰州。
若说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根,那中山桥则是兰州的魂,站在桥上,望着桥下滚滚的黄河水,心中不明涌现一种依恋感。从巴颜喀拉山涓涓汇聚的小流,不远万里的奔向江海。蜿蜒曲折,一分一秒不肯停下追逐的脚步。
漫步于黄河的南岸,感受兰州人独有的水车情怀。一辆或几辆水车
映入眼帘,虽然不如当年的水车那般宏伟壮观,但也玲珑可爱,炎日下,叮咚叮咚的奏响着生命的乐章。
黄河是生命的起源,这里孕育了生命的过程,久而久之,在这里形成了特有的美食。在中国,说起面食,不论东西南北想到的不是馒头,包子,饺子,而是面条。面有百种,可在兰州正宗的面只有一种,那就是兰州拉面。据说,兰州拉面已有百年的历史,若是在外面看见“正宗兰州牛肉拉面”,不用想,绝对不正宗。在兰州,牛肉面是牛肉面,拉面是拉面。不可混杂。
坐在江边的面馆,选择一个靠窗的位置,望着对面的黄河,感受那种“黄河之水天上来”的气势。不一会儿,一碗热腾腾的拉面被端上来了。菜叶经过发酵,其味酸,辣,清香混为一体。兰州拉面不同于南方的拉面,将面混于清汤中,上面只需点缀一小撮香菜,几粒花椒,色香味俱全。颤抖着接过大碗,碗中的面条仿佛是我的世界。牛肉香,葱香,面香,还有辣油香,一股脑的涌上心头,嘈杂的面馆似乎也在这浓香中安静了下来。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应该是指一个地方的风,水,人文,以及最重要的食物,塑造出一款款与众不同的民性与民风。想到西北的人们,他们把荒漠之地的蓬草,融入到自己的食物中。正是因为这样,兰州人才有这样如蓬草一般的生命力。让拉面走过这世间的坎坎坷坷,开放于世间的角角落落。
这个盛夏,我站在黄河边,不想离去。风,携着黄河的气息,使山水环绕的金城展现它宏伟的格局。兰州,欢迎你!
带你走进湖南湘乡
高一(3)班王烨菲
作为一个在浙江上学的湖南人,虽说大部分的记忆都与杭州有关,但在时光的最深处,记忆的起点,深埋的总是与家乡湘乡有关的特别回忆。
我医院里,童年在一团一团的丘陵与一条一条的溪流间度过。那里不是什么发达的大城市,并不高大的一幢幢楼房立在灰扑扑的街边。那时的人们大多还骑着摩托车,“突突”地开来,“突突”地开去,所到之处,,卷起一片纷纷扬扬的尘土。看起来似乎是一片不发达的小城镇模样,但你沿着这条马路再走两步,拐一个弯,另一重截然不同的景象又会立即出现在眼前--道路两旁的建筑忽地退出视野,视线骤然开阔,湛蓝色的天空中凝着大团洁白的云,地上大片平坦的绵延到很远的群山间,清新而纯粹的三种颜色让人感觉像是从尘世走进了仙境。
不仅是特别的景,湘乡特别的食,也给我留下了颇为深刻的印象。湖南地处东南丘陵,地势不高但总有不断的山丘连绵起伏。虽说湘乡位于湖南省偏平坦的东部地区,但也是有一堆一堆的小山丘起伏在平地之上的。多山,就会多林,多林,就会带来特别的食物。酸枣树,就生长在这一丛一丛的丘陵之间。一年暑假,因为碰巧赶上好时机,我有幸观看了一回家中长辈如何运用酸枣制作当地的特色小吃。
夏末秋初,是酸枣成熟的季节。人们提了桶,早早进了林子高二三十米的酸枣树周围早己星星点点落了一地青黄色的、微呈椭圆的酸枣。人们将它们一颗颗捡起,不需要多久,就拾了满满一桶。提着桶回家,将酸枣洗净后,直接将它们连皮扔进高压锅,炖烂,打开锅盖,微酸涩却清香的味道满溢而出,这时候不能光顾着味道流口水,待它微凉一会儿,就要趁它尚存一丝余热,超紧将酸枣的皮一个个剥下来--这时候的它皮肉相互分离,正是最好的剥皮时机。剥完皮的酸枣放在一个盆子里,用筷子不停地、用力地搅拌,直到一颗颗的酸枣互相融合粘连在一起,成为松松烂烂的一团。这期间也要从盆里把酸枣的核一颗颗挑出来,直到最后只剩下酸枣果肉组成的一团糊糊。未经加工过的酸枣,其酸味,几乎是让人酸倒牙齿的,因此,会将小团的酸枣糊糊与大团的南瓜糊糊混在一起,辅以少量糯米、面粉、盐、剁碎的辣椒和紫苏,一起搅拌均匀。之后,拿来一块块干净平整的木板,铺上塑料膜,将搅拌后的糊糊铺平成薄薄一层,在初秋的烈日下暴晒几天,经过一系列的工序,最终就成为了当地人民所常吃的酸枣片。
因为我们一家三口对酸枣片都有别样的喜爱,因此,每当假期结束,临行前夜,不论外公外婆,爷爷奶奶,都要往我们的行李中塞上几包。酸枣片独特的味道,随着年纪的增长也逐渐演变为家乡独有的味道。如果你乐意与我一同走进湘乡,我想带你去看看它的蓝天绿地,品品它独特的饮食文化。
带你走近武汉
高一(6)班姚灵欣
说起来我并不是正儿八经的武汉人,只是故乡离武汉相当近,对它远熟悉于居住了五年的杭州,因此武汉被看作我的“第二故乡”也无伤大雅。回到阔别已久的武汉,无论走在新建的繁华大街,还是昔日的偏僻小巷,我仍感觉自己彻彻底底地属于这里。在远离故乡的大城市里徘徊许久,我还是一个土里土气的老样子。静等于飞速行驶的高铁上,我却越发感受到一种脚踏实地的心情,因都市生活而在脑中紧紧绷紧的弦好像也松弛下来。
和杭州比一比,武汉也并不比杭州差多少。就像杭州有西湖,武汉也有东湖。两者相比,东湖以更大的面积略胜一筹,但拿风情来说,两者是毫无可比性的:西湖如苏轼笔下的西子,东湖虽中无江南水乡女子撑船徐行,但周围的热闹场面,足以与西湖的小家碧玉相较量。最有名的黄鹤楼我仅去过一次。在回家的途中,我也并不会刻意经过它。现在回忆起,记忆里只剩下模糊却高大不可逾越的影子。彼时年幼,况且只在人头攒动的浪潮中打量两眼,剩下的印象只来源于崔颢的《黄鹤楼》了。无论如何,这些都可以旅游再去,但有些味道却像史铁生先生所说,如不身临其境,是再也想不起完整的味道的。
回到家,终于能自己到处逛逛。这才想起来,这样的味道有来自武昌鱼的,楼下小店的热干面,和家里的红烧肉。
热干面好像是武汉人早饭的标配。一碗面,一杯豆浆,就能叫人津津有味地填饱肚子。现在看,窄窄的车道改宽了,但街旁的店却一个也没少,仍像以前那样整整齐齐地码着,红黄绿蓝都淡褪地印在招牌里,和记忆里一点也不差。我总是在上学路上买碗面,走到学校就能吃完。老板和客人很熟,总是给熟客留碗常点的面。有时候他们会发出一些感慨。
“哎呀,你要好好学呀。”
“这么辛苦哇,今天这么早就来了。”
在这个街道里,不用外出上班的人们经常聚在一起,不管是谁家发生了红白喜事,还是什么事都没有,他们风雨无阻地来到这个小门店,嗑点瓜子,或者随便什么,等着孩子一窝蜂地从那个小小的巷口涌进来,给我们发一些云片儿糕、牛皮糖和大白兔。有时候带够了钱,就在旁边买个小布丁(这可不能被外婆发现,她从不让我吃雪糕),斯哈斯哈地吃完,夏天里,吐出的气好像都变成了白雾。
老板和客人都是一个街道里的人,有时候打声招呼,就算没有带钱也可以下次来补。好像就是因为这个习惯,到了大城市里我总是给人添了很多麻烦,往后大概也不例外。这样想来,内心真是无比地愧疚,无论是以前帮我的人,还是现在帮我的人,即使我一改吊儿郎当的作风,他们的恩情我好像一辈子也还不完了。
带你走近重庆
高一(6)班傅逸
中考完的后一天,我便乘上了飞机,前往了"四大火炉"之一的城市--重庆。
刚一下飞机,接触到地面,一股属于七月份的酷热感便穿透过鞋底从脚底心一涌而上,渗透到身体的每个部位。除了难耐的炎热,位于四川盆地的重庆,空气中刮过的湿热的风,使人身体中的湿气难以消散。但这并不会影响人们对重庆的热爱。火锅,这一被人们视为其最具特色的饮食,深受着来往旅客的青睐。带重庆,怎能不领略一下这非凡的川蜀风味?鲜红的汤汁在热锅中翻滚蒸腾,在锅的中央形成深红色的漩涡,缓缓上升的热气形成氤氲的云烟,彼此看不见彼此的神色,唯有友人交谈的声音伴着热汤沸腾的声响交织着,透出喧闹与祥和的气氛。
辣味与食物碰撞出的火花才是这场好戏的真正看点。花椒热烈麻辣的口感自舌尖向口腔四处弥散开来,干辣椒嚼起来清脆的劲道,混着被阳光暴晒后的浓郁香气给味蕾带来独特的刺激。那在体内淤积了许久的潮湿感都在此刻被这股热潮驱散得一干二净,在感到火辣的同时,有让人觉得好是畅快。
重庆除了火锅这一侠气豪爽的特色外,也有许多隐藏在城市每个角落的静谧。在那里,人们留下了时光给予他们的珍贵记忆。
走进一家偏僻的咖啡馆,昏黄的灯光,店内播放的歌手低沉沙哑的民谣,仿佛让时光在此处缓缓的静流。小店不大,门前种着一棵刚好能触到屋檐的树,灼热的阳光钻过枝与叶未遮住的空隙,斑斑驳驳地投射在地面上,像被撒在地上的星星点点的金箔,在被人们忘记了的阴影里,熠熠生辉。
从成都到重庆,从上海到重庆,这些已经泛黄的车票、飞机票被经过的人们留在了墙面上。对过去的怀念,对未来的展望……那些藏匿于心中许久的话语都化作一张张便签留在了这里,被流逝的光阴注目,感动着来往形形色色的人。
在离开重庆的那天,天空下起了雨,倾泻而下。那场雨,洗去了我在初中时留下的失落、伤心与遗憾。在那刚刚逝去的三年里,我感受过喜悦、苦楚、无奈,但一切的一切都将在此告别。茶叶在热水的冲泡中有沉沉浮浮,人的成长在不同的时期,有相遇也有离别。
我乘上飞机,与这被雨色描摹的得缥缈的城市挥手道别。
带你走近杭州
高一(6)班夏翎菲
“东南形盛,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柳永《望海潮》
杭州,浙江省会,居浙北,拥之江之浪,享西子之秀,有满觉三秋桂子,曲院十里荷花,实是欲界之仙都。
出生在杭州,自少不了独属于这座城市的烙印。从西湖的桃红柳绿,西子柔情;至西溪的荻野鹤鸣,曲水风雅。从运河的南北通衢,三地交汇;到钱江的弄潮儿立,大浪淘沙。亦或是红尘烟火,市井人生,那独属于舌尖上的记忆烙印。
桂花藕粉,杭州特产小吃。由鲜藕制作,入口香糯,清甜可口,融着桂花的淡淡香气,可充饥,亦可作为茶余饭后的一份小点。最初结缘,来源于幼时灵隐之游,彼时年纪尚小,最喜甜食。闻到蜜甜的藕粉香气,见他人品尝。便坐在婴儿车中挥手,吵着嚷着要吃。祖父疼我,掏钱买了一份,让母亲一小勺一小勺的喂给我。我也不怕烫,一大口接一大口吞吃,吃饱了,便倒在车中睡了。那日的景是一概记不得了,只在记忆深处,有着一碗冒着热气的桂花藕粉。
定胜糕,相传为南宋名将岳飞的夫人所创。将米粉糕做成元宝形状,上以模具印有“定胜”二字,佐以红豆沙的馅,软糯香甜,很适合游玩时手中捧着一块,边走边吃。而“定胜”二字,又为其增添了份别样的美好喻意。中考前的早饭,便是一块冒着热气的水红色的定胜糕。母亲微笑着送我出了门:“吃了定胜糕,考试定胜,成绩节节高!”兴许是托了定胜糕的福,中考顺利,成绩亦没有发挥失常。母亲将其归结为我的努力,她不知,这亦有她的定胜糕的功劳。
片儿川,杭帮面之首。冬笋,白蘑,肉片,雪菜,配一把龙须细面,武火爆炒,逼出浇头的鲜后加水下面,文火慢熬。面筋到,汤鲜美,蘑菇肉片笋片爽滑,浇头佐面,配一口汤,冬笋,蘑菇的鲜融合的恰到好处,为冬季佳品,亦是母亲的拿手。每次烧面,母亲都要对食材精挑细选,百般打量:冬笋为佳,春笋为次;肉要后腿部的瘦肉,不带一丝膘,蘑菇要带根,不带根都是药过的,不健康……一碗面,常花费母亲半天时间。寒风夜归,一碗片儿川下肚,既暖了身,亦是暖了心。
“重湖叠掩清嘉,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云树浇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这是柳永笔下那个令金世宗都向往着的杭州。而桂花藕粉,定胜糕,片儿川,这些再普通不过小吃糕点,串起我的人生,亦串起我对杭州一点一滴的城市记忆。
带你走进
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个上一篇下一篇

